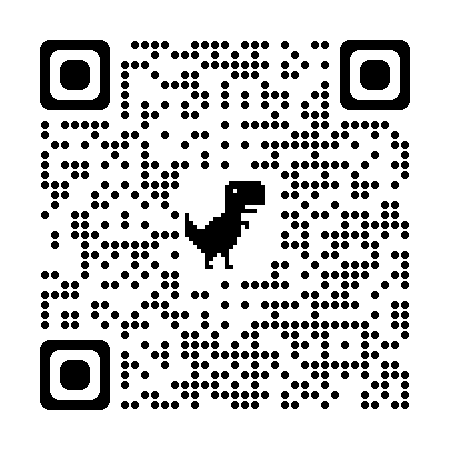周臻的回答
我们先来算一笔账。
以一辆10万元钱的汽车计算,每年的使用成本按照平均1万元计算(包含保险费等),10年后的汽车残值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10年用车总花费大约就是20万元。
20万元的钱如果用来打车的话,确实可以打很久的车,如果按照平均一次50元,可以打车4000次,哪怕每天一次,打车10年,就是3650次,的确花不完这些钱。
这么算下来,买车确实是不如打车划算。
那么,算这笔账很困难吗?其实很简单,上过小学的都能把这笔账算清楚。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选择买车呢?
因为上面只是比较了金钱成本,生活中除了金钱成本, 还有其它方面成本。
1.节省时间
打车需要等待,而自己有车的话就可以说走就走,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等待时间,买车就相当于花钱买时间,而时间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2.提高生活质量
买车后可以提高自己和家庭的生活质量,这是毫无疑问的。日常接送孩子,周边游 ,自驾游,过年过节回老家探亲等生活中离不开的事项开自家的车和打车去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3.心理上的体验更好
开自家的车和打车在自己心理上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而且人是社会动物,你有车没车在别人眼里的看法也不一样,这也是事实。
所以,开自己的车相比打车确实有其优势,可以给人带去很多的方便,而这些方便之处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除非无人驾驶普及了,随时随地都可以方便打到车,那时候或许真的不用自己养私家车了 。毕竟,养车不仅需要金钱成本 其实也有其他方面的成本。



© 版权声明
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相关文章
暂无评论...